不会盖房子的哲学家不是好匠人

“只要拥有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匠人。
“无法将双手和大脑联系起来,无法承认和鼓励人们内心有从事匠艺活动的欲望,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缺陷。”
--理查德·桑内特
不会盖房子的哲学家不是好匠人
摘自《匠人》
文|理查德·桑内特 译|李继宏
- 声明:如需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1926年到1928年,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致力于为他的姐姐在昆德曼街设计和建造一座楼房;昆德曼街在维也纳,当时还有很多空地。维特根斯坦曾自豪地谈起这座楼房,但最终变成了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他在1940年写的私人笔记中提到,这座建筑“缺乏健康”;他怀着郁闷的心情回想起他的建筑,觉得它“很漂亮”,但缺少“自然的生活气息”。他鞭辟入里地为这座楼房的疾病做出了诊断:这要怪他自己最初的想法,那时候“我的兴趣不在于修建一座楼房,而在于……给自己提供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这个计划实在是再宏伟不过了。这位当时年纪尚轻的哲学家试图理解所有建筑的本质,第一次动手就想修建一座完美的模范楼房—如果不算一座位于挪威的小木屋,这是维特根斯坦唯一盖过的房子。它的建造理念是表现出某些建筑的共性,成为“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兴建昆德曼街这座楼房时,维特根斯坦的生命正处于一个特殊阶段的末尾,当时他正在哲学上寻找一种类似于“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的东西;从大约1910年到1924年,他乐此不疲地探索这种通用的哲学理论。我相信他在回头审视自己的建筑时显得如此挑剔,也是因为盖这座楼房浪费了他不少本来可以用于哲学研究的时间。但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那座楼房:根据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判断,他对理想的完美建筑的追求,导致这座楼房变得毫无生气。损害到这座楼房的,正是他的不懈追求。
有个好办法可以评价这座楼房和哲学家后来对其疾病的诊断,那就是将维特根斯坦的房子和同期在维也纳落成的另一座楼房进行比较。那座楼房是职业建筑师阿道夫·路斯设计的。维特根斯坦的建筑品味来自路斯,而路斯的巅峰之作则是摩勒别墅。路斯187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先是短暂地在某个技术学院进修过,然后去了美国,一边当石匠一边上学。他自己的建筑实践始于1897年。他最初是以建筑学方面的著作和设计方案闻名的,但始终对建筑楼房的物质过程有强烈的兴趣。这让他有可能体验到一种较为正面的痴迷,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懈地追求把事情做好,但是也顾及了各种在他控制之外的情况,以及其他人的劳动。
维特根斯坦和路斯的初次相遇,是在1914年7月27日的维也纳帝国咖啡馆,当时他更钦佩的是路斯写下的论著而不是修盖的建筑。路斯把建筑视为新客体,认为应该突出建筑的实用功能,尽量少用装饰。我们在讨论物质意识那一章提到的“诚实的砖块”在这种倡导材料与形式是一体的新客体主义中再次出现,但路斯剥夺了18世纪关于材料的讨论中那些拟人化的联想。他也很讨厌他父母那个年代的房子,空中挂着流苏和水晶吊灯,地上铺着厚厚的东方地毯,架子上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内部空间则摆了许多餐桌书桌,还有碍事的仿古柱子。
1908年,路斯在《装饰与罪恶》中炮轰了这一切。他试图将自己在美国游历时发现的实用之美和建筑结合起来,用一些日常生活用得上的物品来取代华而不实的装饰,比如说手提箱、印刷机和电话。路斯特别敬仰干净利落的布鲁克林大桥和纽约火车站的架构。和他那些在德国发起包豪斯运动的同时代人一样,路斯拥抱了一种由工业生产造就的革命性美学观,这种在《百科全书》中早已露出端倪的美学观和约翰·罗斯金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那些将匠艺和艺术合二为一的机器揭示了所有建筑形式的本质之美。
“干净”和“简洁”很能激起维特根斯坦这种家世的年轻人的共鸣;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在建筑上的品味,以及他在打造“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时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他的家境。他的父亲卡尔当时已经是欧洲实业家中的顶级富豪。老维特根斯坦并不是那种粗俗的资本家。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布鲁诺·瓦尔特和巴勃罗·卡萨尔斯都是他的座上宾;他们会看到老维特根斯坦家墙壁上挂着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其他新艺术家的画作;建筑家约瑟夫·霍夫曼已经完成了老维特根斯坦许多乡村别墅中的一座。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建筑作品
但就像一战前许多富裕的犹太人那样,维特根斯坦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露富,因为19世纪90年代维也纳反犹主义情绪高涨,首当其冲的正是那些爬到社会顶层的犹太人。就以位于阿利街的维特根斯坦公馆为例,其私人空间极尽奢靡,而公共区域则朴实无华,两者达成了一种惊人的平衡。尽管浴室的水龙头都是镀金的,卧室和小型客厅里充满了各种珠宝玉石,但大宴会厅则要收敛得多。卡尔·维特根斯坦买得起任何他想买的画,也买了很多上佳之作,但在这个用来会客的大房间里,他只挂了几幅新艺术家的作品。这响应了针对当年维也纳犹太人富翁提出的“装饰就是罪恶”的口号:用来展现财富的装饰就像厕所里的东西,是上不得台面的。
维特根斯坦虽然不用工作,但是在帝国咖啡馆遇到路斯时,他已经在柏林学习过机械工程,并在曼彻斯特大学进修过航空工程学。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咖啡馆里跟路斯说了些什么,但他们见面后变成了好朋友。维特根斯坦的家财逆转了传统那种师傅和学徒的关系。在这次会面之后,维特根斯坦开始悄悄地塞钱给比他年纪大的路斯。
维特根斯坦家族的财富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建设那座楼房时那种负面的痴迷。虽然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他的财产,但在给他姐姐修建昆德曼街上的楼房时,他用起钱来却毫不犹豫。他的侄女赫米内·维特根斯坦在题为“家族往事”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个颇能反映其挥霍无度的故事:“当时整座房子都盖好了,正要开始打扫卫生,他却要求将某个大房间的天花板抬高三厘米。”这次调整貌似很小,但却涉及庞大的结构重建,只有不惜代价的客户才会这么干。赫米内说诸如此类的改动有很多,都是因为“路德维希一丝不苟地想让所有比例都恰到好处”。经济的约束和阻力并没有成为他的老师,而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又催生了导致他的楼房“生病”的完美主义。
在路斯的建筑中,缺钱往往和简洁的美学观结合在一起,1909年到1911年间他在维也纳给自己造的房子就是这样。他的构思倒不完全是清教徒式的;比如说他给1922年落成的芝加哥论坛报大厦添加了许多闪亮的花岗石柱子,因为他的客户很有钱。等到有钱的时候,路斯也买了不少非洲雕塑和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并将它们摆设在自己家里。他的建筑理论和经济状况促使他选择了朴素和简洁,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客体主义完全拒绝感官的愉悦;对形式的痴迷并没有钝化他对材料的感觉。
路斯必须积极地应对他遇到的困难,这可以从他建设摩勒别墅时所犯的错误中看出来。当时摩勒别墅的地基没有打好,可是他没有钱将其挖掉重来,于是只好加厚了一面墙壁,以此来消化这次错误,并将这面加厚的墙壁变成重要的侧壁。摩勒别墅规整干净的形式,是路斯修正了许多类似的错误、克服了许多现实障碍之后才得到的;资源的匮乏刺激了他的形式感。维特根斯坦因为并不缺钱,所以无缘于这种形式与错误之间的创造性对话。
赋予事物以完美的形状可能意味着抹除工作过程的痕迹和证据。证据被消除以后,物品就会显得浑然天成。这种清理出来的完美是一种静止的状态;物品本身并没有任何痕迹反应它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我们将这两座楼房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它们在墙面比例、房间大小和材料细节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从形式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楼房就像一个四周附带着小盒子的大鞋盒;只有后面那个盒子的屋顶是倾斜的。这座楼房的外墙涂满了光滑的灰色石灰泥,一点装饰品都没有。其窗户的线条非常规整,前立面的窗户尤其如此。这座楼房有三层,每层有三个窗户,每个窗户各有两根窗棂,将其隔成三个同等大小的长方形窗格。摩勒别墅则是另外一种盒子。路斯早年认为建筑应该表里如一,但等到开始建造这座楼房时,他已经放弃这种想法。外墙的窗户大小并不相同,自身构成了一个图案,有点像蒙德里安的画作。维特根斯坦那座楼房的窗户样式大小都很死板,而摩勒别墅的窗户则要灵活得多。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是,路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工地,仔细观察光线在每天不同时段的变化,再据以修改自己的建筑方案。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这么做,所以他的方案也就没有路斯的灵活。
如果走进这两座楼房,对比就更加强烈了。在摩勒别墅的门厅,立柱、楼梯、地板和墙壁的表面都在邀请来客继续往里面走。这基本上要归功于路斯对光线的敏感;这些表面的光线会随着人们的走动而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人们对这座楼房的观感。维特根斯坦家的门厅和入口走廊就没有发出这样的邀请。对确切比例的痴迷导致门厅看上去更像一个独立的房间。原因就在维特根斯坦在此处应用的计算:室内玻璃房门的比例和室外玻璃窗户的比例一样,而地板的比例又跟房门的比例一样。白天的光线只能间接地照射进去,而且分布得很均匀;夜晚的光线则来自一个裸露的电灯泡。人们走得越深入,这种静态空间和动态空间的差别就会越明显。
现代设计师很难处理好单个房间的大小与连接各个房间的通道之间的关系。在古代政制时期,有些贵族建筑采用了安菲拉德设计,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但它更依赖房门的位置而不是房间的大小。现代的建筑师希望人们能够在空间里自由地流动,于是他们将室内的房门放大,消除了墙壁。但安菲拉德的艺术很复杂,并非只是简单地拆除了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障碍,它通过墙壁的形式、地板的高低和灯光的变化来组织人们的流动,这样你就知道要走去哪里,可以走多快,最终走到什么地方可以停下来。
路斯根据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的节奏,精妙地计算出各个房间的大小;维特根斯坦则孤立地从维度和比例的角度去考虑每个房间的布局。路斯的客厅地板错落有致,混用了不少材料,光线也很复杂,延续了门厅发出的邀请,这完全展现了他的精湛技艺。维特根斯坦家的客厅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空间。他试图用一种粗暴的方法来创造流动,把客厅和书房之间的墙壁改造成一扇折叠门,只要一打开两个房间便相互连通;但没有障碍物并不等于客厅和书房是浑然一体的。它们只是两个相邻的、各自独立的盒子。(维特根斯坦拆掉和抬高一英寸的正是这个客厅的天花板。)
最后,两者在材料方面也有区别。摩勒别墅有一些装饰品,但不是很多。墙上的搁板摆放着一些水罐、花瓶和画作;这些装饰品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以免和房间的大小不相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路斯已经打破了自己原有那种追求朴素的观念,开始接受一些简单的装饰品。等到建造摩勒别墅时,他已经大量地使用木质装饰品。
维特根斯坦所用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符合新客体主义标准的漂亮物品。维特根斯坦将其在工程学方面的才华倾注于诸如取暖器、钥匙之类的物品和厨房等地方,而这些都是当年的建筑师不屑一顾的。由于特别有钱,他无须使用市面上常见的东西,一切都是专门定制的。比如说厨房窗户的把手就特别漂亮。这个把手很特殊,因为它是少数根据实用功能而不是为了展现形式而设计的硬件。但这座楼房的门把手再次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对比例的痴迷;各个房间都很高,但所有的门把手都安在地面和天花板的正中间,所以用起来特别困难。在摩勒别墅,路斯根本就没有留心这些硬件的细节;取暖器和管道往往被隐藏或者包裹在木头和石头的后面。
所以这个建筑的例子反映了痴迷的两面性。维特根斯坦的楼房代表着其中一面,这一面的痴迷完全没有受到约束,导致了令人失望的结果;路斯的楼房则代表着另外一面,这位建筑师也很痴迷,但懂得节制,更愿意参与到材料与形式的对话中去,所以他建造了一座足以令自己骄傲的楼房。我们可以说,健康的痴迷会审问其自身秉持的信念。当然,在许多建筑师看来,维特根斯坦的楼房并没有他自己想的那么糟糕。这些人很欣赏他的建筑,拒不接受他后来的评价,认为那是这位建筑师罹患严重的神经症之后瞎说的。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成年人,接受他说的那些话。
在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完美主义给他的哲学和精神生活造成的破坏性效果,那座楼房的种种毛病正好反映了这种效果。维特根斯坦早年写了《逻辑哲学论》,试图给逻辑思维树立一些最严格的标准;多年以后,也就是在他反思昆德曼街的楼房时,他又写了《哲学研究》;这部著作则力图将哲学从那座精神大厦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这位哲学家已经变得对语言、色彩和其他感官的变化备感兴趣,而且他的写作不再为了制定规则,而是为了探讨悖论和比喻,在这样的哲学家看来,追求一种适用于所有建筑的理想形式无疑是“病态”和“缺少生机”的。
我详细地描写这两座楼房,是因为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两面性提供了一些如何在日常劳动中对付痴迷的指导方针。
优秀的匠人明白草案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并不是十分清楚你要做些什么。路斯最初想要把摩勒别墅打造成一座好房子;以往的经验为他提供了一个模板,但在抵达工地之前,他没有更具体的想法。非正式草案是避免不成熟结果的工作程序。而维特根斯坦则不同,想要打造一座囊括所有建筑可能性的楼房,尚未正式动工他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这种形式的痴迷中,一切都以蓝图为准。
优秀的匠人重视偶然性和约束的价值。路斯很好地利用了这两个因素。在讨论物质意识那一章,我们强调了变形的价值。路斯将工地上出现的问题视为机会,所以他让各种物品出现了变形。维特根斯坦既不在意也不理解利用困难的必要性。痴迷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到其他可能性。
优秀的匠人需要避免钻牛角尖,别试图完美地、孤立地去解决问题;否则就会像昆德曼街的楼房那样,各个房间失去了彼此的联系。痴迷于完美的比例导致维特根斯坦家的门厅丧失了这种关联属性。其实更好的做法是允许自己打造的东西有一定的缺陷,而不是追求尽善尽美。
优秀的匠人会避免那种沦落为自我炫耀的完美主义—在这个时候,制造者想要的不是展示他或她做的东西可以干什么,而是炫耀自己能够干什么。这就是昆德曼街楼房的门把手等手工打造的硬件的问题所在:它们炫耀着维特根斯坦的形式感。优秀的匠人则会避免这种故意指出某样东西很重要的做法。
优秀的匠人知道何时应该停止。继续搞下去可能适得其反。维特根斯坦的楼房确切地表明了在什么时候应该停止:那就是在一个人想要消除工作过程的所有痕迹、以便让其作品显得浑然天成的时候。
如果将打造一个组织比喻成修建一座楼房,你会想用路斯的方式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方式来打造它。你不会想要一下子就把它打造得很完美,而是从一个架构开始,把这个架构当作草案,再慢慢地修改。你会想要像路斯那样,让组织内部变成一个相互连通的整体,邀请人们从一个领域走向下一个领域。你会对付各种难题、偶然事件和约束。你会避免让组织里的人承担一些像维特根斯坦的房间那样孤立的职责。你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停止组织建设,有些问题没法解决也就算了,你还会完整地保留整个组织成长的痕迹。你不会通过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来打造这个组织;维特根斯坦已经明白,这种追求导致他的楼房毫无生气。无论你要打造的是学校、企业还是某种专业技能,采用路斯的方法会让这种组织或者技能具有更高的社会质量。
(完)
《匠人》
[美] 理查德·桑内特 著
李继宏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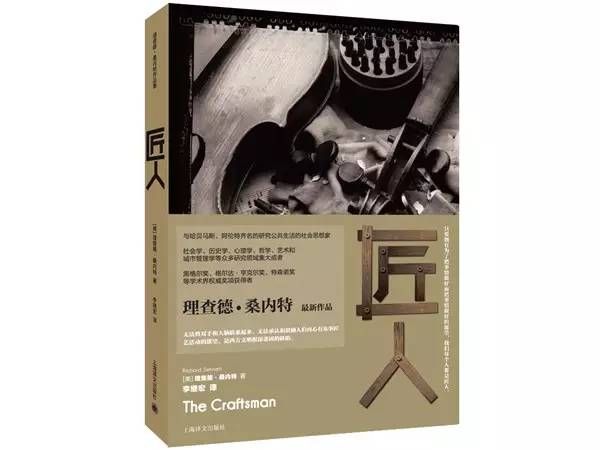
《匠人》要探讨的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纯粹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尽管匠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一种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消失的生活方式,桑内特却认为,匠人的领域远远大于熟练手工劳动的范围;今天的程序员、医生、父母和公民都需要了解匠人精神的价值所在。
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中跨越了时空,从古罗马的制砖工人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从巴黎的印刷社到伦敦的工厂,都是他笔下探讨的对象。
历史在实践和理论、技艺和表达、匠人与艺术家、制造者与使用者之间划下了一道错误的界线;现代社会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历史遗存的折磨。但从前那些匠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匠艺也揭示了一些使用工具、安排工作和思考材料的方法,进而为我们如何利用技能来指导生活提供了各种可行的方案。堪称作者的巅峰巨著。
理查德•桑内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目前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杰出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城市》《阶级中隐藏的伤害》《眼睛的良心》《公共人的衰落》《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不平等世界的尊敬》《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等。
江晓源(交通大学教授):
理查德·桑内特的《匠人》通过追溯自古希腊至现代的历史,以音乐家、建筑师、作家等不同职业为例,讨论匠人与艺术家、制造者与使用者、技巧和表达、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展示了作者的广博只是和学术洞察力,标志着桑内特的文化唯物主义已达成熟境界。
杨宇东(第一财经日报执行总编辑):
对于匠人在文明史中的地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的评价!这本书不止重新定义了“匠人”,更是通过桑内特宏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术积淀,重新寻找到了匠艺的最初起源——基本的人性冲动,是为了把事情做好的欲望;并且,匠人精神不仅帮助人类脱离了洞穴,也是通向科学和艺术的必由之路。
它也是一部极具野心的作品,面对匠艺活动在工业社会中的逐渐式微,桑内特透过条分缕析的讲述,还匠人以尊严:匠人的工作方式使其在物质现实中找到归宿,匠艺活动本有人性的光芒,因为我们“建立社会关系的能力,其实和我们在制造物品时使用的那些身体能力是相同的。”
维舟(书评人):
理想的匠人生活,其实便是理想的人类生活:清楚自己面临的困难在哪里、通过掌握技能去完成自身的创造性任务,桑内特坚持认为“几乎所有人都能变成优秀的匠人”。
如您对这本《匠人》感兴趣,
试试长按下图二维码或戳文末“阅读原文”吧

上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stphbooks”添加关注
文艺连萌
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
相关知识
不会盖房子的哲学家不是好匠人
【怪事】据说这8种坑爹户型不能买?快来你家是不是这样的!
设计师不是零成本吗?怎么还收这么高设计费
【百科】天下最会当老板的人竟然是他!
他们都说房子一定要有客厅,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姿势 |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
买不起房子的郑州人注意了!不用什么大房子,有8平就够了!
花三十年修栋老屋,他们不是修房子,是在享受生活
【百科】绝对不能进微波炉的13样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